2016年起,作家王心钢和韶关本地党史专家梁观福开始筹备创作长篇纪实《赤焰》。他们对北江工农军的历史进行集中学习与研究。作为一支地方武装的北江工农军,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其征战史亦可歌可泣。许多工农军英雄抛头颅、洒热血,将火热的青春献给了革命和人民,值得敬仰。《赤焰》把讲述时间放在1927年4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前后,直到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并重点介绍了周其鉴等革命烈士的背后故事。故事分为三大块:
一是北江工农军是如何建立的,为什么要北上武汉,其中发生了什么;
二是北江工农军是如何参加南昌起义的,又是如何随军南下的,经历了哪些战斗;
三是南昌起义失败后,这些农军战士如何回乡重树义旗,组织暴动,最后随朱德部队参加湘南暴动,会师井冈山。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赤焰》第五章:饮马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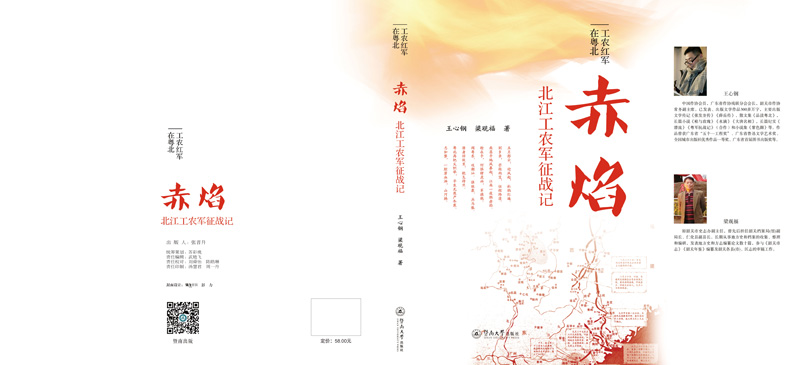
1
湖南永兴,罗绮园一边在督促乐民要做好留下人员思想工作,加强训练,一边在与武汉方面联系,争取部队能早日北上武汉,以摆脱湖南反动军队的魔掌。
6月8日,被总部派去联络的朱云卿回到永兴,说陈嘉祐已和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沟通好,北江工农军可打着十三军教导师补充团的番号,从永兴出发,先乘汽车到衡阳,再由衡阳搭船到株洲,后搭乘火车经长沙到武汉。
罗绮园大喜,要求部队迅速行动。陈嘉祐随即命令沿线部队,要确保补充团的安全,防止遭到长沙反对军队的袭击。
虽是一路有许克祥部队在虎视眈眈,但北江工农军官兵们仍是兴奋不已,毕竟好多人还是第一次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感觉十分新鲜和神速。6月15日,他们经长途跋涉,安全到达武昌,被临时安排在蛇山北面徐家棚的“春草堂”内。
“春草堂”其实是一座花园,占地约有50多亩。园门前“春草堂”三个字据说是康有为的手迹。园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花木茂盛。里面几座平房正好做士兵营房。居住条件相当之好,只是没有操场,练兵不方便,练兵时须到园外公路上,如遇上雨水,道路泥泞,显得美中不足。
部队到武汉后,罗绮园代表北江工农军,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汇报部队由韶关到武汉的经过。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部长、中共党员苏兆征对该部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武汉参加革命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表扬。
6月20日,阳光明媚,部队操练得不亦乐乎。中间休息时,参谋长朱云卿给战士们动员鼓劲。“我们这支队伍从韶关好不容易地来到了武汉,中间经历了千辛万苦。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军人,军人,就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要好好练兵,练好一身本领,将来上了战场,就要真刀真枪地同敌人拼命。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战士们响亮地回答。
周其鉴从外面进来,笑容满面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尊敬的何香凝女士会来探望我们。”
队伍中,有知道何香凝这个名字的战士一听,立刻大声叫好。
周其鉴继续说:“何香凝女士是廖仲恺先生的遗孀,一直紧跟孙中山总理,是同盟会的老会员,国民党的元老,她还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这次,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她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暴行,与其决裂。她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日理万机,能抽出时间来探望我们,是对我们队伍的关心。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训练成绩来报答何香凝女士!”
下午,阳光炽热,何香凝在罗绮园的陪同下来到工农军驻地。何香凝举止端庄,说话温和,对来自广东的工农军嘘寒问暖,讲了许多鼓励的话。其中“誓不与民贼为伍,广大革命党员要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派”的讲话铮铮有力,给了官兵们莫大鼓舞。
何香凝离开驻地时,官兵们行军礼相送,久久不愿放下举着的手……
随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中华总工会和武汉社会各界团体纷纷派代表来慰问看望,送来军毯等慰问物质。《汉口民国日报》先后以《粤中武装农工来鄂》等为题,报导了湖北总工会、妇女解放协会和汉阳各区农会等团体慰问的消息,赞扬北江工农军“不失数千里山河跋涉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斟钦佩”。
6月29日,北江工农军指挥部派出林子光、侯凤墀、梁功炽三个代表,前往中央农民部,报告北江工农军的近况,对社会各界对该部的关心和慰问表示谢意,再次阐明北江工农军到武汉的目的,是在广东军阀压迫下,“为着保存革命的实力,以图拿红色恐怖来打倒白色恐怖起见,所以克服艰难困苦而来革命的根据地武汉”,并表示今后“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初衷而酬雅望”。
2
作为北江工农军总指挥,罗绮园把队伍安全带到武汉后,心里落下一块石头。他此时更关心的是武汉急速变化的政治形势。
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三镇到处可见反蒋的标语,报纸上也每天登载反蒋的文章。革命阵营出现了大分化。南京方面不少反对蒋介石镇压工农运动和不满意其搞军事独裁的革命军官,纷纷脱离蒋介石跑到武汉方面,有些受蒋介石排挤的部队如第二军、第六军,也由南京转到武汉方面。正是在这复杂背景下,第二次北伐誓师典礼在武汉南湖举行。誓师大会后,张发奎便亲率第四军、十一军从武汉出发,于5月1日前全部开抵河南省驻马店,集结待命。
接下来的战斗是一场残酷的恶战。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北伐军最后以付出了一万余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击退了奉军,把河南地盘无条件地交给了冯玉祥。然而,令北伐军官兵们始料不及的是,冯玉祥却是一个“骑墙派”,在他们前脚刚走,马上表示不再支持武汉政府,倒向了蒋介石,而他们的初衷本是希望冯玉祥能与武汉政府合作,共同反蒋的。谁知竟成如此结局,白流了众将士的血。
苏兆征告诉罗琦园,“马日事变”严重地摧残了湖南的中共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它给我们共产党人提供了严重教训,那就是不能满足于表面上数字庞大却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工农武装,必须有自己坚强的革命军队,同时实行攻势的积极防御才是有效的,消极防守坐等人家来打,不预想反击的措施只能是死路一条。
罗绮园问:“那么中央对我们广东工农军有什么安排?”
苏兆征沉默一会儿,说:“对于你们工农军到武汉的事,我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就提出过。为此,该委员会开会专门讨论了相关议题。”说着,他掏出笔记本,让罗绮园细阅相关的两则会议记录: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员会政治委员会
第廿九次会议速记录(节选)
时间: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下午四时
地点:汉口中央党部
出席者:林祖涵、陈公博、汪精卫、孙科、吴玉章、陈友仁、谭延闿
主席:孙科
书记长:陈启修
……
苏兆征:广东来的工农自卫军如何安插?
谭延闿:最好是归并第四军,都是广东人。
主席:请苏部长同张发奎军长商量安插的办法。
决议:照办。
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
三十一次会议速记录(节选)
时间:十六年六月廿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时
地点:汉口中央党部
出席者:孙科、林祖涵、陈友仁、王法勤、谭延闿、汪精卫、陈公博、吴玉章、邓演达
列席者:苏兆征、詹大悲……
主席:汪精卫
书记长:陈启修
……
苏兆征:处置广东工农自卫军的问题,已经同张发奎、陈嘉祐两同志接洽过,他们都愿意要,不过张同志要将他们补充各处缺额,陈同志答应仍将他们编在一处,他们愿意到陈同志那里去。
主席:很好,就是这么办,也不必作决议。
罗绮园对苏兆征十分熟悉。他是广东香山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香港大罢工,历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政治局常委、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国民政府委员兼农工部长,并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虽然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对工农军到武汉之事还是挂在心中。
苏兆征说:“陈嘉祐率领教导师调移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特将第二军教导师、第五师和新成立三十九师合编成第十三军,由陈嘉祐任军长,下辖第五师、第三十八师和第三十九师,驻守湘南地区,负责对广东、贵州方向的警戒。你也看到了,在安置北江工农军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有两个意见,一是安排到张发奎的第四军,二是安排到陈嘉祐的第十三军。但张发奎提出将你们分散安排到部队中以补充缺员,无形中打散了你们的建制;而陈嘉祐对你部十分熟悉,又是他把你们带到武汉来的,因此,他同意保留你们原有建制,作为其属下一个补充团,每月给你们6000元津贴费。”
“我部上下都愿意到陈嘉祐部,这样才能确保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武装不被打散。”罗绮园说。
苏兆征说:“陈嘉祐已任命乐民为十三军补充团团长。组织上决定任命你为国民政府农工部秘书长,叶文龙则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育长。同时朱云卿,我们也将调他到武汉农政训练班工作,你看怎样?”
“很好啊,我毕竟是个秀才嘛,不是带兵的料。”罗绮园笑着说,“至于朱云卿是个未来的将才,更该重用才是。”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北江工农军虽然编入国军序列,但实际上还是由我党领导。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都清楚他们是工农武装,对他们相当关怀,决定发给部队慰劳金一万元中央纸币,给每个战士发两套军服。”
“太好了,官兵们一定会高兴的。他们会服从党的领导,积极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罗绮园对工农军能“修成正果”,感到由衷的高兴。
苏兆征对罗绮园说:“你离开部队前,要找乐民好好谈一谈,告诉他现在国共关系有走向分裂之势。汪精卫已有些动摇。唐生智已宣布拥汪反共,现在我党可靠的部队只有二十四师叶挺部,十一师周士第团和武汉警备团。张发奎或不反对我们,至于陈嘉祐,现时态度还好,不过他的部属多是湖南人,将来恐怕不大可靠。工农军是本党重要军事力量,一定要掌握好。党中央正设法将他们调入城内,随时准备应变。”
乐民当日即跑去武昌纸坊十三军军部面见陈嘉祐。
陈嘉祐见乐民到来,虽脸露笑容,但眉宇间显有隐忧。“怎么样?你部到武汉还习惯吧?”
乐民说:“部队官兵情绪向来很好,日日都在抓紧训练。日常训练工作由副团长李资负责。驻地是一座大花园,环境优美,可惜无操场可用。”
陈嘉祐听罢,说:“现在国共两方似不甚融洽,将来演变如何,很难逆料。不过你尽可放心,不论环境怎样变化,我都要庇护你们,我绝不会做出对北江父老不住的事情,尤其是你本人,我对你倚望正殷,将来我必定设法提拔你。”
他点了支烟,又说:“昨日罗绮园同志来过,谈及你们的驻地不便训练的事,我已商得警卫团方面的同意,将跑马场的营地让出给你们,此地与军部较为接近,以后联络一切都便利得多。我已告诉沈参谋长,日间即有命令给你。”
“那真是太好了。”乐民知道陈军长事多,起身告辞。
翌日8时起床,团部干部都来问乐民,外面的消息如何?他们看来极为关心时局的状况。乐民告诉他们:“本团即将移驻武昌城内跑马场。”他们听了大为雀跃。当天下午,果然传到部队移驻武昌城内的命令。
部队进驻武昌后,除了练兵之外,还注重加强政治和思想学习。朱云卿亲自给他们上政治课,特地抽出一天时间,带领大家到武昌起义始发处(中华民国政府鄂军都督府)参观,现场讲述武昌起义的故事。
讲到黎元洪当年操练新军时,朱云卿语气凝重起来。“黎元洪在操练新军时,将新军操练得很有成果。我想,我们北江工农军一定不会比黎元洪的新军差,大家有没有信心?”
战士们齐声高喊:“有信心!”
许多战士站在庄严的都督府面前不禁浮想联翩,想起在家乡闹革命时的情景,那是多么地痛快淋漓。而现在远离故乡,穿上军装肩负重任,其中不仅有亲人重托,更有自己的信仰。
军人,就是为战争而生,为和平而生。“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诗人王昌龄的名句,正体现了战士们此刻心情。
3
夏季的武汉热得像只大火炉,烤得人不动也在不断冒汗。市民们晚上都不呆在房里,男女老少一人一张凉床,全都跑到露天里睡觉。而从广东来的工农团战士更受不了这闷热蒸烤,恨不得整天泡在水里才好。
此时,比天气更闷热的是武汉的政治。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送给汪精卫看,幻想争取汪精卫的同意。汪看后暂时没有表态,但已种下了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种子。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应冯玉祥的要求,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国民政府部长的职务。
7月的武汉大雨连绵,新的洪峰在长江上游酝酿。中共中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改组,由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履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停职。鉴于汪精卫集团已在公开地准备发动政变,中共中央于7月13日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决定与共产党正式分裂。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大革命宣告失败。国民党多次反革命政变的事实,打破了北江工农军原来所怀的美好革命理想。全团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甚至有点人心惶惶。有些干部甚至脱离工农军,投奔到张发奎的部队中去。
刹那间,呈现出一派“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困境。
其时,陈嘉祐忽然下令,十三军补充团长乐民改任团政治指导员,另派参谋长沈凤威兼任团长一职。
在这种情况下更换军事主官,引起官兵们许多猜测。周其鉴就表明反感的态度,因为沈凤威曾在北江镇压过农运,是个臭名昭著的反动军官。好在沈凤威心不在此,来了不几天又调离补充团,仍由乐民以政治指导员兼代团长,主持全面工作。官兵情绪才稍微安定下来。
7月21日,周其鉴和乐民接到中共中央密令,要他们迅速脱离陈嘉祐十三军,将队伍开赴南昌集中。
他们当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将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只是认为宁汉合流之后,中共采取的一种行动。不过,他们也从其他渠道得到“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分子与贺龙,叶挺军队在南昌另组革命委员会。提兵南下广东,讨伐李、黄、钱、邓诸逆,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农民,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与南京政府对抗”的消息。
然而要离开武汉去南昌,并非易事。作为团主要负责人,乐民不得不做郑重考虑。一方面,北江工农军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能不服从上级命令。另一方面,该部又同时属于第十三军补充团,如果不遵守军令而擅自行动,会被以叛军罪论罪,要遭到军法和严厉处分。更何况武汉近郊驻扎众多国民党部队,北江工农军红色标志明显,若是私自离开部队,给其他部队发觉,必定会被追击。以北江工农军区区600余人,经不了人家几下打,很快就会被“包了饺子”。
乐民想来想去,想出一个自认为较好的理由。他亲自登门找军长陈嘉祐协商,说土兵们因在武汉水土不服,导致不少人患病,加之农民观念太重,离乡日久而生思乡之情,一个个都在闹情绪想回家。能否请陈军长恩准,同意北江工农军离开武汉回广东家乡?
陈嘉祐一听有些意外,他与北江工农军关系很深,感情融洽,知道该团官兵都很年轻,基本上是二十岁左右青年人,大部分有文化,革命情绪很高,懂纪律,比一般军队官兵素质强许多。当前正是扩军用人之际,哪里舍得让他们走?
陈嘉祐说:“别轻意说走吗,有什么事不能解决?我去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果然,陈嘉祐以军长身份亲自到部队驻地,给全体官兵训了两次话,希望官兵们继续留在十三军,为完成北伐的使命而共同奋斗。陈嘉祐训话时,言词恳切,讲到激动之时,不禁声泪俱下。官兵们也深受感动。
周其鉴在一旁听着,感慨万端。北江工农军自5月初追随陈嘉祐教导师入湘,虽只有两个多月,但得陈嘉祐帮助不少,由于他驻韶关有年,对工农运动素来热心和关注,与北江革命同志合作得非常紧密。入湘后,工农军常得到他的照顾,驻地必选择最安全的地方。部队经过长沙时,他亦派军掩护,确保万无一失。到达武汉后,官兵们都希望能继续追随于他,为革命事业而努力。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时局变化出乎人意料之外。彼此之间虽有不舍,但又必须分离。毕竟,陈嘉祐部从属于日益走向反共的唐生智集团,而工农军是共产党的部队,必须服从党的指挥。此时摆在工农军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革命就是生路,不革命就是死路。所以只能心底里对陈军长说一声对不住了。
陈嘉祐见工农军去意已决,知道再挽留也无济于事,毕竟这是一支以中共为主的队伍,形势不允许。他也不想同中共发生冲突。他同中共领导有很深的交往,知道工农军说水土不服要回广东只是一个借口,其中肯定有更重要的原因。他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只好答应好聚好散,绝不会干涉工农军的自由,何去何从由大家自己决定。
乐民见陈嘉祐同意后,便命令部队赶快做好准备,以最快速度离开武汉,开赴南昌。临行前,他交代,全军在脱离第十三军时,要将陈嘉祐当初拨给的枪械全部退还,好让陈军长有个交待,也不至于让那些对他有成见的人抓住把柄。
这个命令让好些工农军战士想不通。欧日章就跳出来反对。“我们曲江农军的枪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没有枪还算什么军队?不如回家当农民算了。”
周其鉴出来做工作:“我们表面上说是回广东,600多人带着枪走目标太大,弄不好会被其他军队连人带枪一窝端了去。更何况到了南昌回到自己人的部队,何患无枪?”
这一解说,官兵们渐渐明白过来,默默把心爱的枪再擦拭一遍,依依不舍地交了上去。
陈嘉祐对工农军这个义举感到欣慰,密令部队放行,确保补充团秘密撤离武汉。
陈嘉祐后来一直不愿意和蒋介石合作,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迫其居地常迁。1935年陈嘉祐迁居香港,两年后病逝,终年56岁。后妻儿遵嘱,将其安葬湘阴南泉寺。这是插话。
7月29日一早,600多名北江工农军官兵从武汉分乘三艘小火轮由长江顺水东下。码头上挤满张发奎准备东征的部队。
时值夏秋之初,水流湍涨,两岸青山不断朝后飞去。官兵们心情激动,无暇顾及秀丽景色,恨不得一下子就到达目的地。黄昏时分,部队安全到达江西九江,并在市区宿营。这里是张发奎东征大本营,布防严密,不能久留。
第二天一早,北江工农军转乘火车到达南昌,一下火车,就有人员前来联络,随即编入叶挺第二十四师教导团(即七十二团)驻扎在新营房。随队伍到达南昌的工农军负责人有,卓庆坚、周其鉴、乐民、李资、甄博雅、宋华、卢克平、林子光和李甫等人。
队伍刚一驻扎下来,叶挺就派人前来慰问。叶挺是北伐名将,工农军官兵早有耳闻,对其相当佩服,现在能编入叶挺铁军中,心情更为激动,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只是没想到,他们即将参加的是一场名垂青史的南昌暴动。


扫一扫,关注广东残联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