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杨晓婷有很多的“标签”。她是广东省第一名使用盲文试卷参考普通高考的考生;是一个专升本的全盲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是一名残疾人运动员……
人们习惯用标签定义一个人的成败。但摘掉这些标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障碍时,如何在一个完整多元的社会中,努力成为自己的故事。
讲述这个故事,并不是希望更多人为运动员鼓掌,而是看到残障伙伴在“健全视角”建立的社会中如何突破种种瓶颈,社会需要填补什么缺口,去给更多人创造可能。
一个“励志典型”出现的意义,是审视社会做得够不够多,能不能更多,去支持“典型”成为“普遍”。
即使无法看到任何一点光亮,25岁的杨晓婷还是想走一条“更不好走的路”。“我总是想走多一步。”她说,“因为总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出现。”
虽然已记不清自己到底在哪一天终于陷入完全的黑暗,但她记得6年多来,自己每一次踏出的“多一步”:不仅仅是走出失明阴霾的一步,还是学习盲文一年考上大学的一步,成为自行车运动员获得广东省残运会双人自行车项目两块银牌的一步,顺利专升本的一步,以及成为广东省残疾人铁人三项队运动员的一步......
每一步都没有踏空,是因为视力的障碍对她来说已不足为患。“如果没有失明,我可能还是那个不敢挑战、按部就班的乖乖女。”而失明后,她尝试了各种别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其实这些还蛮平常的。”杨晓婷笑着说,灵动的大眼睛里闪着亮光,令人难以相信她没有任何光感,“我想,是障碍激发了我的潜能,让我看到自己的更多可能。”
在她的经验里,她强调自主与独立,面对障碍的方式是不停挑战、不停对抗,最大限度消除障碍给自己带来的不便。但她同时也知道,对抗障碍往往并不能只靠个体的努力,需要社会不断建立、完善支持体系,提供更多匹配有障人士的资源和便利,这也是她希望从一名“励志全盲女孩”往残障研究者、行动者成长的原因。
“我想有机会为残障朋友做一点事。”杨晓婷说,带着微笑和坚定。
 成功摆脱”旱鸭子“身份的杨晓婷。
成功摆脱”旱鸭子“身份的杨晓婷。
“只要有机会,我就想尝试”
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的游泳馆,广东省残疾人铁人三项队正在这里训练,备战将于2025年在广东、香港、澳门三地举办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残特奥会”)。
杨晓婷在引导员的指引下,一步步迈入泳池里,嘴里还欢快地和引导员打趣。下水后,她认真地练起尚不熟练的自由泳,努力克服着视力障碍带来的方向感缺乏。引导员偶尔陪伴在旁,为她掌舵,大部分时间她要自己探索。
这样的练习每天重复进行,最长的时候一次性持续2个小时以上。五个半月来,杨晓婷成功摘帽“旱鸭子”,从一个经过多年学习也学不会游泳的人,成为既懂蛙泳又能游自由泳的游泳新手。
 和队员们一起吃饭的晓婷(左)。
和队员们一起吃饭的晓婷(左)。
她还记得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心里有多慌。“本来脚踩不到地时就很慌,加上看不见,心里更没底,偶尔旁边经过一个人碰到我一下,我就彻底被吓到了,一呛水、又扒拉不到边,感觉太无助了,真的想哭。”
她形容自己一开始笨拙的样子,“不断呛水,呛着呛着总算学会游泳了,但是学了两个月,我发现自己还是要贴着边道游、手碰到墙壁才有安全感,于是向张兆政教练反映,他让我换一道,贴着水线游。”因为看不到,一开始在水里她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游,往往一游就歪,甚至“打横游”。
 晓婷正在整理衣物,准备出发训练。
晓婷正在整理衣物,准备出发训练。
“正式比赛的时候,就会有一条引导线绑在我和引导员之间,她会带领我往前游”。因为看不到,仰泳的时候她常常一股脑子撞到泳池上,手臂上也经常有各种挥到水线或者蹭到水线留下的淤青。
“不怎么痛,队友们不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杨晓婷欢快地说,“但是我的进步好快的。”她对自己的进展不无骄傲,又暗暗下定决心,“下一个目标是提升自由泳。”
 晓婷和队友们开心唠嗑。
晓婷和队友们开心唠嗑。
每天的训练还包括跑步和骑车。“一开始跑步,连一公里都好累人,跑完后连走路都疼,边练边想放弃。”话音刚落她又连忙笑说“就是反复有这个念头而已,脚下可不敢停”。
慢慢地,当跑步从一个小时加到两个小时后,从1公里、5公里到10公里,她“觉得自己还能练,还能进步”。每周一次的测试中,她的成绩不断进步,欣喜之余,她知道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还有8个月。”她对自己充满期待,“我想有机会冲击残特奥会。”
 杨晓婷(右)在引导员的指引下走向泳池。
杨晓婷(右)在引导员的指引下走向泳池。
成为一名铁三运动员是杨晓婷从来没想过的,因为自己没有“童子功”“年龄就摆在那”,甚至连游泳都不会,而体育又如此讲究天赋与积累。但是她再一次以新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又好像是如此理所当然。
在过去的6年里,她不断“变换赛道”,人们不断更新对她的认识,媒体打上了“励志”的标签。
可她知道,她只是在成长为本应该成为的自己——从广东省第一名使用盲文试卷参考普通高考的考生、商务英语专业大学生,到残疾人自行车运动员,从社工专业本科生,到残疾人铁三运动员,在这期间,她甚至成为一名实习社工,学英语、学滑板......
“只要有机会,我就想尝试。”她说。
 正在练习游泳的晓婷。
正在练习游泳的晓婷。
“人可能往往只是低估了自己而已”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杨晓婷的眼睛并不是先天性失明,“我的视力的丧失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晓婷在引导员的指引下走出游泳馆,前往田径场。
晓婷在引导员的指引下走出游泳馆,前往田径场。
初中的时候,她的眼睛确诊出视网膜色素变性,医生说她以后可能会看不见。“那时真的很害怕,每天都在想以后看不见了怎么办,学习的时候想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用眼,但是又担心不用眼的话成绩掉得厉害怎么办,不知道要不要跟老师、同学说这个情况,说了会不会被当作特殊的人对待......”
种种思来想去给她心里带来很大的负担,“有很多不能说出口的小秘密在心里来来回回地,说不出口,我无法接受事实,也不知道我可以得到什么支持。”面对未来可能会看不见的预期,以及因此带来的各种担忧和焦虑,她的眼睛恶化得更严重。
 铁三队队员一起前往田径场。
铁三队队员一起前往田径场。
慢慢地,2017年左右,她的眼前越来越模糊,白茫茫一片,后来只有一些残影。
“每一次变化我都问自己,还会更严重吗。”
她已经记不清具体是高二时的哪一天,自己完全看不见,也不愿意过多形容自己当下的感受,尽管可以想象伴随黑暗彻底来临的,是恐惧、悲伤、失落,甚至是绝望。
 晓婷(左)和引导员做训练前的准备。
晓婷(左)和引导员做训练前的准备。
休学在家的那一年,原来的同学都在备战高考,她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开始偏离了他们的方向,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上大学的机会、成为一名“普通人”的机会。“小时候我想过自己未来的方向的,因为喜欢语言,想要学小语种。”杨晓婷说,“但很可惜,这个梦想应该不能实现了。”
但为什么要用世俗的评价体系,定义“普通人”和“成就”呢?
但如果要跳出过往的评价体系,摘掉“标签”,这个社会有这样的“土壤”吗?
幸运的是,她很快又找到梦想开始的地方。随着参加广州市融爱社会服务中心组织的盲人独立出行的培训,接触到许多“不一样的人”,她开始“重拾生活的希望”,并且有了目标:学习盲文参加普通高考。
 晓婷在引导员的带领下骑行。
晓婷在引导员的带领下骑行。
“有个目标在那里,我才有事情做,才不会想太多东西。”杨晓婷解释自己6年来从来没有停过一步的动力,“视力障碍带来的最大障碍其实是心理上的,不断学习,让自己感觉可以掌控自己,是最好的抵抗障碍的方法。”
对于她来说,这是一种“弥补”,弥补视力的不足带来的不便利,它同时也是一种“对抗”——
“在我看不见之后,会听到很多声音,‘这个你做不了’‘那个你可能有困难’,我就想,看不见怎么就一定做不了呢,换一种方式就可以啊”,杨晓婷对此不以为然,“人本来就有很多潜能,可能往往只是低估了自己而已”。
而认知上的标签,也会导致真实环境处处不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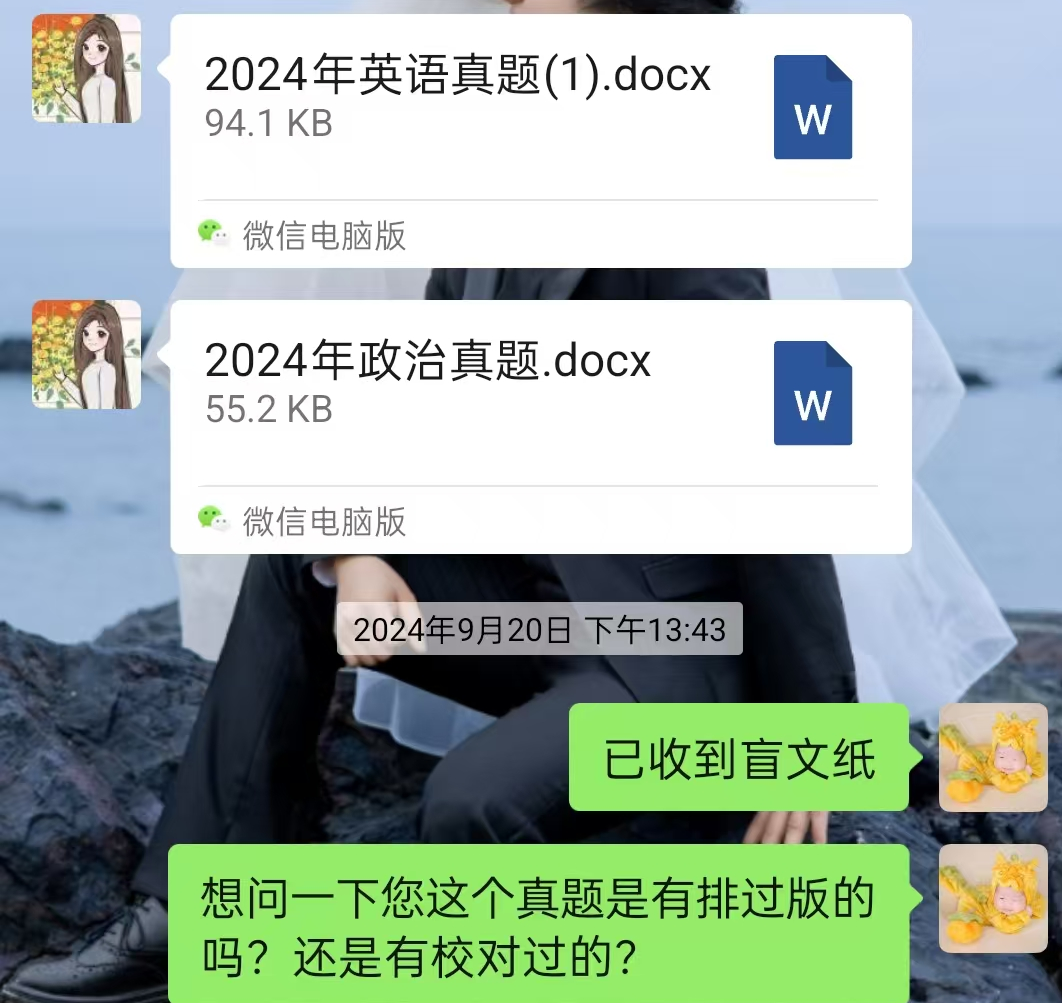
有一次,晓婷需要打印考试题练习,但不知道哪里有盲文打印机,于是主动找到广州图书馆馆员蔡东恺,但广图是后来才引入盲文打印机。那时,蔡东恺工作之余找到广东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学习盲文打印机操作并打印题目。
包括晓婷在内,一些视障伙伴的在细节上的障碍突破,主要是靠民间的善意,但这些无障碍的方法如果没有纳入到一座城市的公共服务框架里,便很难衍生更多关于“共融”的故事。
更多时候,健全视角构建的社会支持体系只是聚焦于个体的“障碍”——大家觉得障碍的根源在于个体而不在于环境,所以健全人被鼓励探索自己,获得各种支持和引导,而“障碍”始终是残障人士的“一生”,而没有从环境去改变。
可如果不再把“残障”视为感动的载体,当聚焦在无障碍环境和技术的支持,个体全人成长的培养,一个残障伙伴,才有可能创造真正的可能性。
 训练中的暂时休息。
训练中的暂时休息。
与柔弱的外表不符的坚强斗志并非与生俱来,从小就是乖乖女的她形容自己从来不敢挑战任何事情,也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因为失明,自己的人生会按部就班,稳稳当当,但是看不到后,好像一下子“放飞自我”,有一股强烈的内驱力推动她去打开自己、探索更多可能性。
“我没有觉得自己跟大家不一样,我只是眼睛看不见而已,我跟别人是平等的,甚至我会努力做得比别人好。”
但杨晓婷也知道,更多的残障伙伴其实被“框住”了,人生不止于“障碍”,可怎么做,才能让个体的成长变得不再“励志”,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关键。
 铁三队正在进行骑行训练。
铁三队正在进行骑行训练。
“每一次转折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每一次转折,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杨晓婷笑着说,轻描淡写。
考上大专后,她跟普通大学生一样体验了充实丰富的大学生活,临近毕业,很多人问她“毕业后能就业吗”,她反问道“难道我只有就业一条路吗?”其实,她一早已经做了决定,继续升学,“我想给自己带来更多可能性,增加自己未来的筹码”。
 晓婷在引导员的带领下与队友们一起跑步。
晓婷在引导员的带领下与队友们一起跑步。
因为曾经得到过社工机构的支持,体会过社会工作专业的“助人自助”“生命影响生命”的价值观所带来的力量,她也想成为一名助人者,暗暗发力备考本科院校的社工专业。
等待本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看到广东省残疾人自行车队招募运动员的消息,她非常心动,即使没有骑过单车,仍鼓起勇气第一时间报名,“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尝试失明后没有接触过的运动项目”。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她进步飞速,被教练挑选参加广东省残运会的双人自行车项目,与队友拿下两枚银牌。
 晓婷努力练习跑步中。
晓婷努力练习跑步中。
顺利完赛后,她收到了本科录取通知书,在继续训练和读大学之间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就是到学校接受全日制教育”。
以同样的坚定加入到铁三队,经历5个月的艰苦训练,再一次实现“零”的突破,杨晓婷心里清晰知道“下一个赛道”在何方:“如果能顺利参加残特奥会并且完赛,我想继续升学。”
她已经定下了明确的学校、专业、方向,想做残障领域的研究,为更多残障朋友做一点事。
在杨晓婷的18岁之后的生命里,人生没有障碍,只有可能无限。


扫一扫,关注广东残联微信